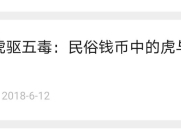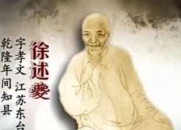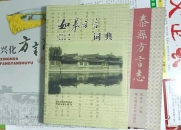走上庄后兴姜河大桥前,首先映入你眼帘的肯定是河南岸的那棵楝树,在这遍地农作物的河畔,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印象中它似乎与我年龄相仿,我瞅着它渐渐长高长粗长得越发秀丽,在见证它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慢慢变老了。
1978年,我高中毕业后到生产队干了几个月农活,有时乘船下田得从它身边经过,那时它只有向日葵杆子粗。待到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我每隔一两周必须运送猪粪下田。午后,它默默地注视着我一竹篙一竹篙将船撑向远方,傍晚又笑迎我返回。那时它已有膀子粗了。
1998年,水利部门在顾庄东北角的兴姜河上架设了一座水泥大桥,名顾四大桥。楝树在大桥西边十来米处。大桥建成后,方便了村民下田劳作,也将北边村庄与顾庄东北角连接起来了,从此原本沉寂的角落变得行人络绎不绝。我闲暇时常在大桥上朝看日出,晚观夕阳落山。那时它已成了一棵大树。
也就是从那时起,附近的居民多了一个乘凉的地方。站在桥上我看到河南岸没有其它树木,就连一些常见的灌木都被清理掉了,唯有这棵楝树傲然挺立在岸边感到好奇。
热心的村民告诉我,此处原是生产队的秧池。当年水网地带的人们出行离不开船,到县城去得坐4个多小时的轮船。一年365天,每天上下午都有固定的轮船从此经过。再因我们这里的土壤结构松散,轮船经过时浪头从远处席卷而来,裹挟大量泥沙,有一部分被带至河心,更多部分滞留河边,使得河床抬高。除了汛期,正常情况下船靠不了岸。为此,每年开春都要人工开挖又深又宽的水槽,这样船才能靠到岸边。但有时河水浑浊,或遇不熟悉情况的人撑船,就不一定能看准水槽而偏离方向。于是生产队干部便挖来一棵树苗栽在河坎上便于人们辨认方向。这样一来,哪怕是晚上,人们也能准确入槽。这棵树便是今天所见的楝树。
后来,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这棵树也自然划归承包户。1998年调整承包地,它又换了新的主人。可是不管主人是谁,一直没有人动过砍伐之念。
如今,四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小伙子已成了头发花白之人,而河边的这棵楝树却进入生长旺期,树高三丈,壮如水桶,树冠向四面伸展,整个树像一柄撑开的伞,浑身透出蓬勃朝气。
暮春时节艳阳高照。午饭后,我信步走向兴姜河大桥。那时正是“菜花落尽豆花开”的时节,田间到处都是或浓或淡的绿色,十分养眼。
刚走上南边的引桥,一股淡雅的香气飘进鼻中。这香味分明不是蚕豆花的味道,蚕豆花气微香,味淡,而这花香味与槐花极其相似,我估计楝树开花了。抬头一瞧,果不其然,楝树花开得正盛,那一朵朵、一串串、一簇簇淡紫色的小花掩映在嫩绿的叶子之中。微风拂过,楝花轻轻摇曳,散发出的淡雅清香,引得蜜蜂和蝴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为午后宁静的河畔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走上大桥,我与树冠的距离近了些,香气更浓了,真是“人近花香浓”啊!
转眼间,初夏到了,那天再次来到桥头时,只见珍珠似的绿色果子挂满枝头,楝树显得更加秀丽庄重。从主干上延伸出的分枝,一层层、一片片,姿态各异。有的分枝先向上托起,然后平铺开来,直面苍穹,展现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有的则向四周张开,宛如温情的母亲搂抱身下的孩子。枝的上细枝嫩叶相互交织,疏密有致,这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件放大的盆景。
楝树不仅美丽,而且浑身都是宝。它的树皮、叶、花、果实都有不同的药用价值。小时候为了驱蛔虫,不少人服用过楝树根煎的汤。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供销社土特产门市部,每年秋季都收购楝树果,虽然一斤只卖二分钱,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利用课余时间打楝树果卖的钱,可抵得上一个壮男劳力一天的报酬。所以那个时候的楝树果是挂不到正月半的。除此之外,楝树的木材质地优良,适合制作家具、建筑、耕地的农具、车船和乐器等。它的边材呈黄白色,心材呈黄色至红褐色,纹理粗而美观,手摸如玉,有光泽,又易加工,深受青睐。
过去人们栽种树木更多的是看重其实用性,因此,有条件的人家便在房前屋后栽种一些可利用树,而楝树尽管实用性上更胜一筹,则很难入选。盖因楝树,也叫苦楝。因为它的根是苦的,果实也是苦的,而没有人愿意吃苦果,所以它被当作一种“不祥”之树,也就很少有人家在自家附近“自寻苦果”。
兴姜河边的这棵历经六十余年风雪雨露洗礼的楝树是幸运的,它能存活下来,是因为得到淳朴村民的保护,因而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