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出书很容易,因为出版业市场化了。出版商捧着书号叫卖,只要花钱就可以圆你的出书梦,这无疑带来了出版业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有出版社580多家,每年出版文学类图书5万多种,其中大约有85%是自费出书。可是让自费出书者尴尬的是他们的书印好后直接拉回家了,有的还没拆封就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自费出书大致有这样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单位供职或者是从某个岗位退下来的同志,他们可以依靠积累的人脉拉到赞助。书出版后有推销的途径,不但个人经济效益可观,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影响力。另一种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完全是自己掏钱出书,他们的书推销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是免费赠送亲朋好友。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出现这种现象不足为怪。从科学的角度看,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一种产品,如果没有经过流通领域,就不能成为商品,所以就没有使用价值和生产价值。出版业也不例外,它同样要遵循投入和产出这个经济规律。一本书出版后,如果没有人购买,也就失去了出版的价值。当然自费出书对出版商是没有影响的,他们的原则是首先保证自己盈利,而不会顾及对社会造成的浪费。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世旭在《话说出书》这篇文章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一个人本来就不具备某一方面的能力,或者创造力枯竭,明智的做法是另择为社会服务的途径,而不是增加社会的消耗。有鉴于此,我给自己立下一条原则,就是决不花钱出书。这并非是因为我的书好出,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清楚自已缺乏市场影响力,从不会为难任何出版社,当然更不会为难朋友。”陈世旭的这段话不仅仅是告诫想出书或已经出书的人要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应该说陈世旭是一位对读者对社会负责的作家,否则他的作品也不可能获奖. 纵观中外文学史,留下传世之作的作家都是厚积薄发。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是法国伟大的作家,他从1890年开始酝酿这部小说,到1912年完成最后一卷,前后化了20多年时间。更让人感叹的是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遥,长篇小说也只有一部《平凡的世界》。但它是精品,成了广大青少年的必读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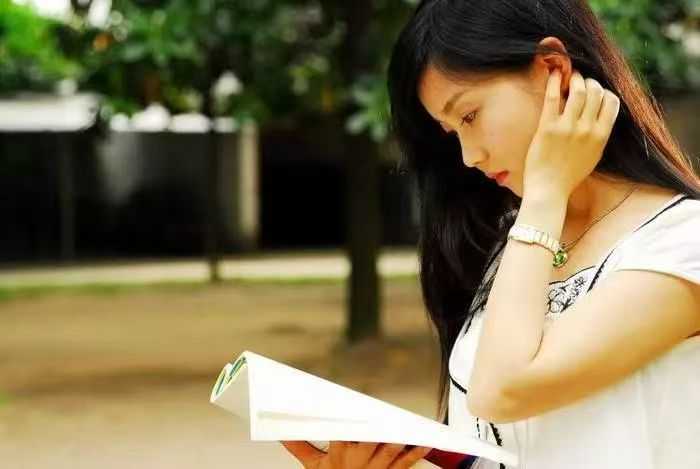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少数“网红作家”一年可以写三四部长篇,结果是胡编乱造,甚至抄袭剽窃。即使有媒体爆炒,还是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市场是无情的,也是很公平的。我们的作家包括业余作者,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任何带有功利色彩的东西都不可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著名作家巴金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是因为他“掏出自己的心”来和读者交流。面对巴老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不是太浮躁了。 或许作品的数量可以扩大作家的知名度,但优秀的作家追求的不是数量,而是读者喜欢的精品。以小说《活着》蜚声文坛的作家余华曾赴美讲学半年,回来后感触很深。他说这次美国之行最大的感受是“惭愧”。在去美国之前,觉得自己至今没有写到200万字,在中国作家中是“低产作家”。然而到了美国之后,在兰登书屋里看到的那些令人崇拜的大作家的作品比他还少。余华说:“那时我更惭愧了,原来欧美的作家是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写一本书,而我们的作家是用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一年不出一个长篇就简直活不成了,这怎么能一样呢。”余华的感慨至少能让我们的内心有所触动。(原载《盐阜大众报》)
编辑:吴勇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