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自强晚年
痛苦岁月 宏愿难施 张謇的晚年,是在军阀混战的痛苦岁月中度过的。他痛恶军阀混战,然而他为了通海一隅之地的苟全,却不得不与各派军阀联络周旋。他认为发展实业、教育需要和平、秩序,而和平、秩序有赖于各级政权的维持。因此,他总是尽一切可能寻求各级政权的庇护与支持。1916年袁世凯病死以后,各派军阀之中暂时还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够以武力统一全国。中国已经再一次失去自己的政治重心,军阀混战就是这一政治态势的体现。以张謇为代表的东南地区上层绅商,已经不再幻想贤良的中央政府的出现,而只是企望通过联络个别军阀头子以保持局地区的安宁。
张謇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中,煞费苦心地应酬周旋于相互以立争战的各派军阀之间。1919年以后,他曾先后担任过皖系政府的扬州运河督办,直系政府的吴淞商埠督办、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副委员长之类无足轻重的闲职,并且让儿子孝若先后出任过直系政府的出国考察实业专使与驻智利公使(未到任)。同时,他又同意把华成、裕华两个盐垦公司的经理朱庆澜、陈仪,调到奉系军阀那里分别担任北满对俄军司令和高级幕僚,以后朱庆澜还曾就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等要职。1922年,张謇命张孝若以答谢各界人士为他庆祝70大寿名义,先后到洛阳、奉天访问吴佩孚与张作霖。张謇这些活动的意图,就是同时敷衍激烈对抗的两大军阀集团以图委曲求全。这不是张謇有什么过人机智,倒正反映了他的处境特别艰难。

1922年张謇庆祝70大寿时与道贺的各国来宾合影(前排右8为张謇)
1924年,直系军阀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遭致惨败,连一向盘踞江苏并与张謇关系较深的齐燮元也“下野”了,这就使张謇更加感到无所凭借。1925年,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迅速把势力扩大到江苏各地。于是,张謇又加强与孙传芳的联络。这年冬天,孙传芳为了笼络与利用江苏上层绅商,特地乘专轮到南通访问。张謇只能表示热烈欢迎,据说,在张謇父子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有一道别出心裁的“华盛顿汤”,借以表示对于“孙联帅”的良好祝愿。张謇就是这样艰难地在军阀重重矛盾的夹缝中求得苟安。直到1926年,大概他感到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才没有继续进行劝和活动。
张謇这些翻来覆去的劝和活动,从来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效果,而每逢军阀战争终于大打起来以后,他又只有劝说交战双方尽量“缩短时间,缩小范围,毋滋蔓以增民仇怨”。他希望军阀最好不打仗,如果打仗,最好打得少一些、小一些、快一些。如果有那派军阀打败了,张謇又立即劝他们赶快下野退隐或出国游历,以免引起新的战争。张謇晚年谋求国内“和平”、“统一”、“秩序”的活动能量不过如此而已。
张謇直至晚年仍然不愧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没有忘记维护民族的尊严。他对于欧战以后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浪潮感到触目惊心,特别是对于日本侵略者表现出更多的不满与警惕。他呼吁各派势力停止内争,捐除成见,勉趋一致,共同对外。在外交上,张謇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协定等等正义主张,都是值得赞许的。公理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离开实力而向帝国主义列强乞求正义,正如劝说军阀停止混战一样,无非是徒费唇舌。
当时,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存在着真正为公理而斗争的新的力量。但是很可惜,张謇对于这种实力却存在着疑惧以至对立,因而他晚年的政治活动便游离于历史主流以外。在张謇一生的最后10年,世界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变局。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1919年,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马列主义的传入并且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的整个革命面貌为之一新。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以“五卅”为标志的全国范围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运动的迅速高涨。一场新的更为雄伟的革命大风暴迅速酝酿成熟,时间距离辛亥革命不过十多年,恰好与辛亥革命距离戊戌变法的时间跨度大体相当。如果说,张謇为了理解辛亥革命和支持民主共和,曾经付出了10年以上的时间;那么,他一生的最后10年,还不足以使他理解与同情新的思想潮流与革命潮流。
老骥伏枥 夕阳无限 胡适早在1929年冬天,曾如此评价过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做了30年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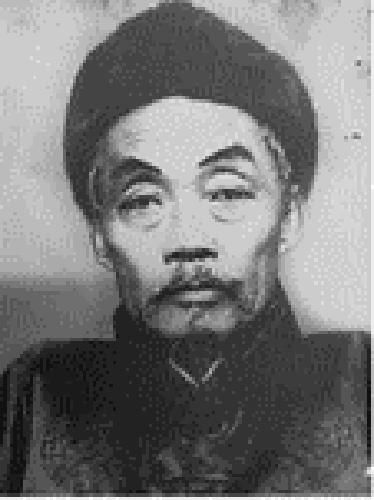
晚年张謇
实业是张謇一生事业的主体。大生企业系统虽然在张謇生前即已破产易手,但这无非是产权的转移,他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各种企业,毕竟为通海地区的近代化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张謇尽管晚年实业顿挫,但他仍然继续扶持南通教育事业的发展。1920年,他已将医、纺、农3个专业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1924年,他又向美国政府谋求退还庚子赔款资助南通教育事业向高层次发展,包括完善南通大学农科设备,工科增设印染专业,水利交通添设河海工程,商业从中专提高为大学,文科分设哲学、经济、历史、地理四个专业等等。同时,他仍然极端注意普及国民教育。就在这一年,他向前来南通参观的日本青年介绍:“南通现已有初级小学校三百余校,鄙人尚拟扩充至一千所以上”。直到1926年最后病倒之前,他还参加了南通女师范二十周年纪念并发表演说,又撰写了《女师范纪念小学校记》。6月间,也就是病逝前一个月,他还参加南通全县童子军会操,并且发表演说:“鄙今日希望于南通童子军者,即就童子军现有之规律,能切实做去,以养成将来军国民之人格,并非希望将来吾通出一督军、师长”。这竟仿佛是他留给青少年的恳挚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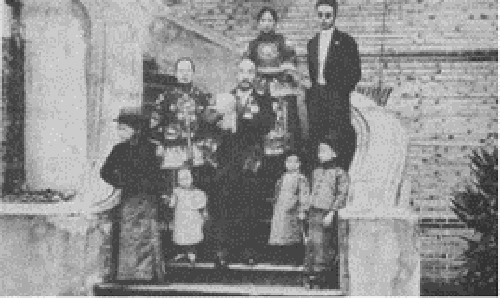
张謇与全家人在濠南别业楼前合影
张謇由于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所以他非常重视培养和运用科技人才。张謇尊重科学爱护人才扶植新建学术社团,提倡科学应该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正确方针,因而赢得科学家们的敬爱与推重。他与许多一流科学家建立了友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1922年8月18日,中国科学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奉献给张謇,以表彰他对科学的倡导与支持,题词说:“本社名誉社员张季直先生,耆年硕德,利用厚生,科学昌明,群资先导,同人敬献生物研究所,以志纪念”。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当中,只有张謇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
张謇认识到医药关系到国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因此也极力谋求改良和发展。他主张引进西医学说以辅中医之不足,设立医校的宗旨也正于“沟通中西”。他还发起修订《中药经》以发扬《本草》之学。他想以私人力量,用科学方法,在三五年内修成一部新的中药典。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不过张謇关于中西医相互沟通,以及首先加强中药的药理研究与药剂规范化的主张,都是符合医药事业发展规律的。
张謇又非常注意国民体育锻炼,他所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课均与其他学科并重,并且在南通先后建筑两处公共体育场。每逢全县开运动会,张謇必定亲自参加,并且发表演说给以评判。他对军事体育特别重视,提倡民兵制度,期望能够逐步实现:“民不畏兵,兵不侮民,兵与士相出人。是以军以礼而国有威,人有兵而士可将。”这当然是针对军阀割据、混战的痛苦现实而提出的改良主张。1922年,他在南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指责中国军队的腐败,他希望通过运动会上的“动作进退”,考察学生平日所受教育如何?自治精神如何?以及“不竞意气不好小勇”的器量如何?提倡体育运动的目的,仍在于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提高国民素质,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军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尊重知识 广交艺友 张謇对于发展社会教育,亦称民间教育,也花费了极大的精力。除公共体育场外,他创建了博物苑、图书馆、伶工学社、更俗剧场以及城南五公园、唐闸公园等等。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希望能为南通居民提供一个优美而又富有教育寓意的社会环境。
张謇创建博物苑,是由于参观日本东京帝国博物馆受到启发。访日归来以后他曾上书张之洞,请求在京师建立帝室博物馆,并渐次推广于各行省。张謇并未等待政府的倡导与支持。在光绪三十年(1904),就在通州师范学校校河对岸,迁荒冢千余并居民29户为基地,营造公共植物园,面积30余亩,这就是南通博物苑的前身。第二年,张謇在植物园的基础上开始规划与营建博物苑,并且为之书写楹联:“设为痒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张謇很善于用人,大生纱厂依靠沈敬夫、吴寄尘,垦牧公司依靠江导岷、章亮元,都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内素。博物苑的主任一职,他选择了通州师范的优秀学生孙钺,此人在博物苑工作近30年,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可以说是把一生都献给了博物馆事业。
张謇为人高见卓识,他把戏剧改良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他即打算训练京剧演员,曾对梅兰芳说:“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之嚆矢。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又可断言者。吾友当知区区之意,与世所谓征歌选舞不同,可奋袂而起助我之成也”。只是由于梅兰芳感到培养戏曲演员困难甚多,而且又要到日本演出,此事才暂时搁置下来。
张謇与梅兰芳交谊始于民国初年。1914年,张謇到北京政府任职,公务之余自然有更多机会观京剧名伶演出。这一年11月19日,就曾“至公府陪宴观剧”,在总统府看了当时已经相当走红的梅兰芳的表演。所以次年6月18日“有观梅郎戏艺作此诗”,第二天又“有重赠梅郎五绝句”,可见“梅癖”渐深。1924年,张謇已逾古稀之年,仍然不忘与梅兰芳探讨京剧表演艺术的改革,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时梅兰芳正筹划组团赴美演出,与张謇商讨有关事宜颇多。

在南通张謇与梅兰芳合影
据说,“梅兰芳三次到南通,张謇礼遇甚隆。每次都特派专轮接送于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如梅兰芳第一次来通,张謇当日就于更俗剧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会,并安排他住在自己的别墅——濠南别业,并将著名剌绣家沈寿女士设计,女工传习所师生日夜赶制的淡青色绸底,绣满梅花的绣幅,赠给梅剧团,梅兰芳离去时,张謇又亲率南通各界以及军乐队送至‘候亭’。第二次,第三次均是一如既往”。这不仅是给予梅兰芳个人的殊荣,也是对于整个表演艺术的高度尊重,特别是对京剧艺术推陈出新的厚望。在当时把听戏当着纯粹消遣,借“捧角”宣泄声色之欲的鄙俗气氛中,社会上能够真正从艺术上理解与呵护京剧演员如张謇者能有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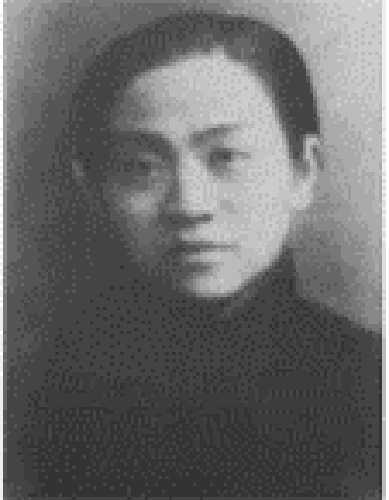
戏剧家欧阳予倩像
张謇对欧阳予倩的交谊,也是中国戏剧史上长期流传的美谈。张謇对戏剧改革的关心,决非只限于某一出戏或某一演员,他是谋求最能代表中国歌剧的京剧的整体改革和根本改革。1919年,梅兰芳访日归来,张謇曾写信对他说:“一方订旧,一方启新;订旧从改正脚本始,启新从养成艺员始”。就在这一年,他邀请戏剧家欧阳予倩到南通创办伶工学社,同时又建造了更俗剧场,作为戏剧改良的开始。
1919年5、6月间,欧阳予倩来南通演出,张謇特地前往观戏,并就创办伶工学社事有所商谈。欧阳予倩果然不负重托,他于同年7月与薛秉初等前往北京招收30名学生,派人送往南通。欧阳、薛随即前往日本考察东京帝国剧场,并访问了东京舞台顾问小山内氏。同时,张謇命徐海萍借南公园布置校舍,置备戏校教学与生活用品。欧阳予倩回国后,又在南通录取30名学生,9月中旬伶工学社即正式开学。更俗剧场亦同步进行,于11月1日落成。张謇亲任伶工学社董事长,张孝若任校长。教师也大多是从上海请来的优秀人士,如昆曲名宿薛瑶卿等,京剧名角芙蓉草等,文化教师则有春柳社创始人吴我尊等,多为当时文学、话剧、音乐、舞蹈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欧阳予倩教授京剧、话剧和艺术概论等课程。张謇还亲自为学生讲修身课,批阅学生的书法习作,并对书法成绩优异者给以具体指点。
张謇推崇梅、欧阳,不同于一般达官贵人庸俗的捧场“或杂以猥下亵视之意”。他是艺术家的知音,而且自己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戏曲艺术的革新潮流之中,他与戏曲的剧作编导、表演艺术家、乐师美工人员,都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与语言,堪称是京剧艺术的真正知音。
张謇对剌绣艺术也是情有独钟,他热爱与扶植剌绣艺术,也是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史上足以长期流传的佳话。

一代绣术大师沈寿像
早在宣统元年(1909),为筹备南洋劝业会,张謇负责主持审查展品。当时,湘、鲁、江、浙绣品云集,商部派绣工科总教习吴江沈寿前来参与审查。沈寿带来自己的佳作意大利皇后像,精美绝伦,展出后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沈寿在审查工作中认真负责,挑选精要,作风严谨。张謇对之极为推重,次年即送女生赴京从沈寿学艺。辛亥革命爆发后,绣工科解散,沈寿逃兵出京。张謇惟恐她的高超技艺失传,便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绣工科,聘请沈寿为主任,其后又另建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仍由沈寿主持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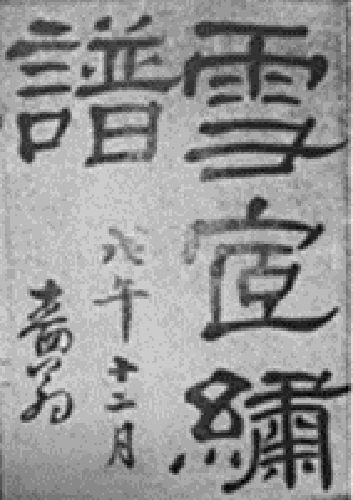
图为沈寿口述、张謇整理的《雪宦绣谱》
沈寿精于绣术,堪称一代大师,她对学校教授管理均为严谨,南通妇女入学者甚多,成绩颇为卓著。但是她体弱多病,张謇借宅供她养病,又“惧其艺之不传而事之无终”,乘她病况稍有好转时,由她口授张謇笔录,“审思详语,为类别而记之,日或一二条,或二三日而竟一条。次为程以疏其可传之法,别为题以括其不可传之意。语欲凡女子之易晓也,不务求深;术欲凡学绣之有征也,不敢涉诞”。花了好几个月时间,终于写成《绣谱》一书。沈寿以病弱之躯在南通执教8年,学员结业者150余人,其中优异人才有9人,使沈派天香阁绣法得以流传。张謇对沈寿,正如对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一样,寓理解于爱护,是对艺术和美的尊重,也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珍惜与力求发扬,这正是张謇不同于市侩俗吏之处。
沈寿本来就体弱多病,加以多年创作、教学的呕心沥血,终于积劳病重,虽然张謇夫妇多方延医摄护也难以挽救其生命。1920年正月,沈寿病情迅速恶化,医治无效,终于五月三日子夜逝世,享龄47岁。沈寿死后,张謇根据其遗言,为之公葬于黄泥山南麓,墓碑书曰“美术家吴县沈女士寿之墓。”
足迹归踪 灵伴五山 张謇的一生是无比勤劳的一生。他的时间与精力固然是有限度的,但他在事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追求却是无止境的。直到1926年他已经是73岁高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工作仍然是相当忙碌的。他的日记告诉我们:
阴历正月初四,当家家户户仍在充分享受节庆欢乐的时候,张謇已经过问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工程,4天以后又亲自前往工地观察。
二月二日,前往“路工处议公共汽车事”,为发展南通现代交通操劳。二十三日,派人分别祭扫特来克、张景云、沈寿三墓,这都是帮助他建设新南通的重要功臣啊!二十四日,与沈同午讨论开筑新运河事。二十八日,“……分三千亩之地于两师范学校”,实即购买沙田产权作为维持两校生存的基金。
三月六七两天,先后参加女师20周年校庆与女师同学会并发表了恳挚的演说。九日,去海滨垦牧乡视察工程及“五堤定界”,十一日冒雨归来。……长途劳顿归来不过3天,他还不忘请著名花匠来教园丁种兰。二十八日,县童子军会操,他应邀前往观操并发表演说,这是南通童子军第一次会操,却是他最后一次演说。
四月一日,参加垦牧公司股东会。十四日,“往剑山视工,大风。”二十二日,到唐闸参加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常会。午后又参加大赉董事会,还会见了前来访问的英国水师提督嘉美麟司令、少将高梅伦、军需书记白昂。二十八日“通海官绅会勘县界,至老洪港。”
五月一日,“至东林看稻畦,西林看东桥工。”三日,“往丝鱼港定通、如、海县界”。十五日,嘱人协助无锡杨令茀女士书画会陈列。十六日,“保坍会十七楗沉排,往观,雨阻于西山村庐。”
六月进入高温季节,气温高达华氏百度左右。他的身体已感不适,但十六日仍参加剑山文殊院落成典礼。还至姚港视察十八楗工程。到二十三日起,觉得遍体发热,也不以为意,次日清早还偕同了工程师去察看江堤,计划修建很紧急的石楗。二十九日下午,病势渐重,人才支持不住就请了平日常医病的俞、金二君诊脉,都说脉象虚滑,暑湿夹痰,来势汹汹,很是担心。于是,当晚电邀上海宝隆医院德医白鲁门托克博士来通,诊断为胃肠炎,吃了一点药水,当夜回沪。次日又请了上海奥医赖司赉博士平治,诊断为心脏衰弱,连打强心针。又请了中医沙健庵、刘祖权二先生来珍,说暑湿内陷,恐怕要脱,渐入险境。又请了朱君芑臣来运气,按摩三次。陈君端白新从德学医返国,奉了他父亲陶遗先生的命到通省视诊治,和奥医仔细商量用药。
七月十四以后,一天比一天险迫起来,家人至戚,固然人人愁泪相对,束手无策。十五、十六两夜的月亮很佳,天空没有一丝浮云,家人跪地求天保佑。十七日中午,这位为发展近代实业、教育奋斗了一生的老人,终于最后闭上了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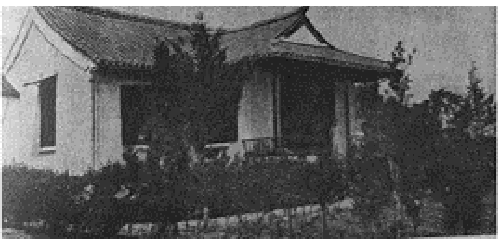
1917年张謇在黄泥山麓建“西山村庐”
张謇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各处的挽唁函电,如雪片而来,许多地方,不约而同的开会追悼,举国都有木坏山颓的哀感。同年十一月一日出葬,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树上,愈感澈亮,寒肃之气,侵入肌骨,好像老天有意给张謇一个光明冷峻的结局。素车白马,四方来会葬的,和地方的人,共有万余人,都步行执绋。凡柩车经过的地方,那沿路观望的乡人,有数十万都并屏息嗟叹,注视作别,送张謇到他的永远长眠之地。

图为张謇出殡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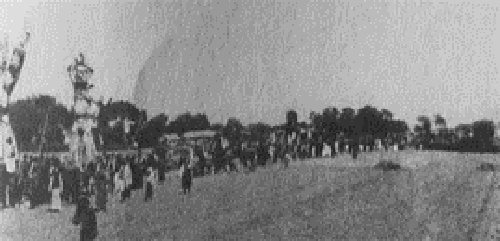
图为张謇出殡时沿途十数万人都步行执绋,肃穆相送,屏气嗟叹
张謇的坟地是他生前自己选择的,已经种了不少树木,前面直对着南山。墓上不明不志,只在墓门横石上,题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之墓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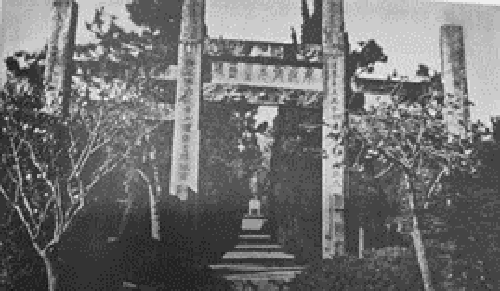
张謇墓不铭不志,仅在墓前横石上题写“南通张先生之墓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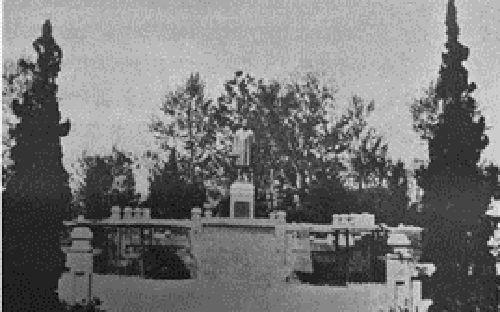
张謇墓地生前已定,南郊袁保圩,墓地已广植树木
全书终
作者:邹迎曦、陆碧波 编辑:吴勇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