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庐笔记】:为什么说越穷越要祭祖,不能马虎 O许石林

【一】孔庙 看了一组拍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照片,很美,但这一组照片,拍得与孔庙、国子监没有关系。乍一看,跟怡红院似的。 拍孔庙、国子监,尤其不能止于拍表面的浮华瑰丽,而应该拍出气象。 如宋人晏元献云:言富贵者当见气象,而动辄金银珠玉,正乞儿相也。 当然了,如今的孔庙、国子监除了文物价值,今人并无气息填充,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越穷越要祭祖 今天的妄人,轻视忽弄丧祭,视礼仪为迷信迂腐者,应该看这一段古人云: “贫人不肯祭祀,不通庆吊,斯贫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絶,是与祖宗不相往来;庆吊絶,是与亲友不相往来。名曰独夫,天人不佑。 ” 【三】西湖六
夯州西湖边上的六树被挖走,换成月基花,引起了夯州市民哗然。外地如这样多少年也去不了杭州一次的,也纳闷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不用问,这就是有人想有所作为了。
曾国藩说:为官欲有所作所为,固然。而书理未明者,未有不妄为也。
阎锡山也说过:事每有不误于糊涂而误于精明者,祸每有不闯于胆大而闯于胆小者,罪每有不成于反抗而成于服从者,此皆知浅不知深,知近不知远,知利不知害之所致也。

【四】最后一代 《谭嗣同与妻诀别》。谭嗣同说,告诉后来的人们我为了什么而死。谭妻李闰说,可是我们还没有孩子。谭嗣同说出了最绝望的一句话:“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个奴隶吗?”
见人在微博上转发这句话,不禁评论道—— 这种话,作为绝境时用于宽慰则可,不可因谭嗣同其人之伟之杰而使后世效仿。一时权宜之言,未为永例之范。

其二,《杨绛:人老了才会明白,最亲的人不是老伴,也不是子女》 其实,杨绛先生固然值得尊敬和缅怀,但“爱而知其”。这老太太的弊病是太刻薄,为文说话非要打通四面墙壁,存心不厚。 凡事无不有其弊,生儿育女也不例外,但人类就是能克服其弊病、忍受其弊病而生生不息、瓜瓞绵绵。如果像杨先生这样发其弊而扬之,则使人尽见其弊,以偏概全,容易误导凡人。 “望人太深则生怨,察物太明则致憎。”杨先生与钱钟书先生都是至察至明之人,一生逞才任智,察物太明而害物,可惜!

【五】 一个自然人,生性必偏左。而通过教育、读书矫正,使其偏右,从而最终归于中正。 当代人普遍不爱读书、功利现实,于是普遍偏左,以激进、二杆子劲儿代替智慧和理性。 宋朝一向被观念向左的当代人看不起,认为不够凶悍霸气。 可是,宋朝有一位江西籍的进士在广东当官,主持司法,他写道: “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汉唐恶足以语此哉?” 大意—— 多了不起啊!我大宋列祖列宗!能够接受并容纳正直的言论,由此养成了臣下个个刚强不屈、正直磊落的风气。朝廷一旦对人才贬斥或升迁不得当,或一旦政令有不便百姓之处,各种各样的正直言论就会全都聚集在朝堂上,士大夫官员们人人都向朝廷进献自己的忠诚,即便是遭遇雷霆万钧的愤怒威力也是不愿躲避的。这种风气,即使是从前汉唐号称盛世,难道可以与我大宋相提并论吗? 当代人偏左的一个表现,就是很推崇强悍霸道的秦朝,认为一言不合就干仗才是真强大。 同样是这位名气不大的宋朝人,居然很看不起秦朝,他说: “周之士贵以肆,秦之士拘且贱。士生于秦,士之不幸也,而于秦乎何益?以是知皋、夔、稷、契知效忠嘉为当然。至夏商之季,亦逢、干所愿哉?” 大意:周代的士大夫身份地位高贵而且言语行为不拘谨、很放达。秦代的士大夫们不断地受到限制而且地位低贱。士大夫生在秦代是士大夫的不幸,而残害读书人对于秦国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可知虞舜时期的皋陶、夔、稷、契等人,以向朝廷进忠献效为己任。而夏代末年的关龙逢和商代末年的比干难道愿意被人宰杀吗?他们也是以向朝廷奉献衷心为己任,可是他们的命不好,生错了时代。 2022年5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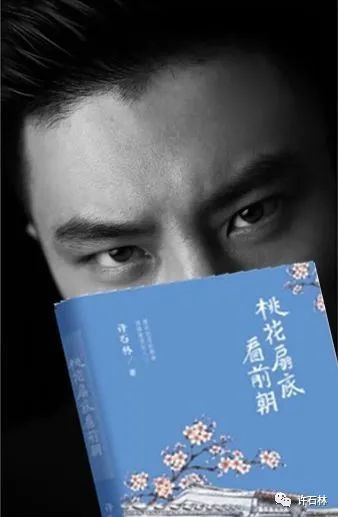
荐稿:刘根勤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